一场大雪像是一条洁白的哈达围在州城大街小巷的脖子上。由于雪大路滑,街道上出租车比往常少了许多。为了去参加朋友聚会,我边走边挡车,已经是第十一次招手了,眼看着车子又一次呼啸而过。
等不到车,无奈只好步行,走出一里多路,心情愈发急切,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守时的人,宁愿我等人,不愿人等我。雪花急急地飘着,身后的商洛大剧院里传来我最喜欢的商洛花鼓唱段《天狗吞月》,心情却未有丝毫的平缓。
站在中心广场的街边,冷飕飕的风夹杂着雪花呼呼的灌进脖子里,若在往常,我这个一向喜欢浪漫的人,或许还能矫情地伸出手感受一下雪花的亲吻。可此时此刻,只有一个感觉“冷”,我也迫切地需要来一条柔软、温暖的哈达。还是没有打到车,脚却冻得生疼,像是光脚板踩在冰碴子上。
正当我冷的要爆粗口时,一辆出租“嗞”的一声在我身边停了下来。“陈队长,你到哪呀?快上车,把你捎上!”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我到领航酒店。”我下意识地回了一句,向车里望去,副驾驶上已经有人。我知道叫我“队长”的肯定是“里边”出去的人。我还在犹豫,他又热情地说“快上车,快上车,外边冷的把人鼻子能冻掉。”瞌睡遇见枕头了,我拉开车门,一头钻了进去。“陈队长,你可能不认识我了吧,我是咱老三队的。我那时在咱队上磨水晶球。” “哦,想起来了,那时候他们把你叫栽怪”,迟疑了半秒,我接过他的话。“嗯,就是我,你还记得2008年那场大雪,中午在操场开饭时,我和赵乐开玩笑,趁他不注意,我给他脖子里塞了个雪蛋蛋,那家伙恼了,把我追的满院子打。结果他一个仰绊,把手胳膊绊伤了,三天都没有出工,队上要处分我,最后还多亏你给求情,改为批评教育,没有扣我分。要是扣了分,最后一批减刑就毕了,我要多坐一年。”“呵呵,十年前的事了,我都记不得了。”我笑着说。“那时,你在队上,对我们很好。每次周清,你就会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给我们讲的周处除三害的故事。那时,我村子的人背地里都把我叫祸害。”见到我,他好像见到久违的老朋友,絮叨个不停。
“你开出租还行吧?”我关切地问道。“好着呢,我出来后,和我老表合伙买了这辆出租,现在正装修房子,准备腊月结婚呢。”“哦,那好的很,祝贺你。”听他这么说,我突然有一种负重前行,瞬间轻松的感觉。他又开始絮叨,“磨了半年球,我当上了咱队上的质检员,整天和那些老板打交道,没少绊砖头。”“是呀,那时产品的质量也确实是由人家老板说了算。2008年那场大雪过后,原来积压的几十万个次品球,经过简单地修复,全部卖出去了。”“陈队长,你在城里时间长了,你看买啥瓷砖好呀?”“哦,这个你问对了,听说也是咱里边出去的刘强在城边上开了个建材城,他哪儿的磁砖不错,性价比高。你去找他没问题。”“好,好,谢谢陈队长,你的电话号码多少?”正说着话,领航酒店到了。
我给他留了电话,准备付钱。“陈队长,你是我的大恩人,我咋能收你的钱,谢谢你还来不及呢。”话还没有说完,他打转方向,车子“嗞”的一声,消失在茫茫雪雾里。
望着车子远去的方向,我禁不住喃喃自语,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遂拉紧衣领大踏步向酒店电梯间走去。吃饭的时候,我还在一直想那个栽怪,在想,我是一场雪,亦或一条哈达,曾经覆盖了他的一段人生。
(供稿:商州监狱 陈斌)
![图片[1]-陕西省监狱管理局:那人那事-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acbc3a54d7081135.webp)
![图片[2]-陕西省监狱管理局:那人那事-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607ce44185b2d407.webp)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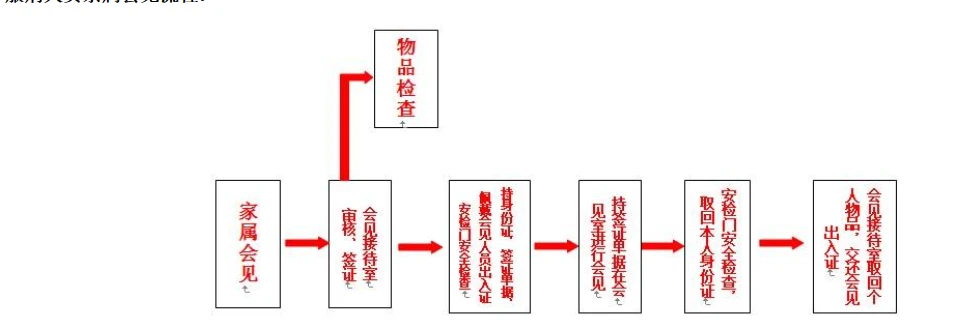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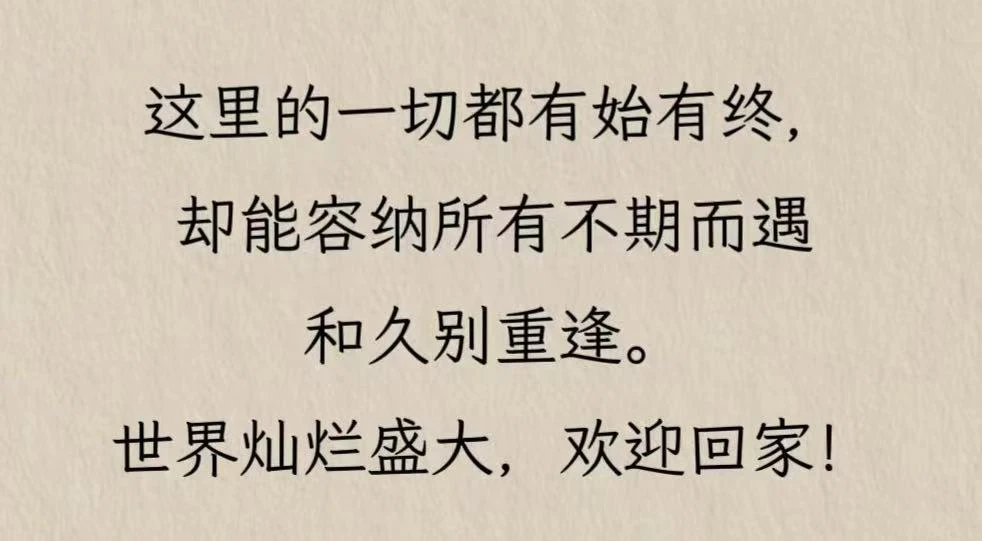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