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外甥女,她说起想找一根老枣木,我在一旁突然想起,我家的老屋的后院,有两株枣树,我小的时候,有茶杯那么粗,现在40年过去了,应该有碗口那么壮了吧,于是,和外甥女夫妇,来到朝邑镇堤浒村,生我养我的村子,也是常常在梦中一次次梦到的地方。 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锁,老屋呈现在我面前 ,老屋有150年历史,门房是撅口厦子,高的外墙,是门房的承重墙,里面有几根木柱子起主要的支撑的承重,两边的山墙早在30年前就被两邻居,盖房子折掉,后又临时胡乱垒起,古代山墙多是公墙,相邻两家个占一半。老屋的门房最早有个照壁,后来拆了。老屋被分割成3个区域,和大门对的是过道,旁边是灶房,占了一少半地方,推开灶房的格子古式门,仿佛又看见母亲忙碌的身影,母亲每天就像变戏法一样,天天给我们做出最好吃的饭菜,即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一碗碗手擀面,筋筋的,细细的,下面时,大火煮一煎,仅仅一点葱花,就是人间美味,没有蔬菜,各种野菜,面条条,灰灰菜,荠菜,刺蕨,人翰,猪毛菜,苦菜,扫帚菜,蒲公英,白蒿,用开水一过,撒些盐和花椒面,就是可口的菜肴。端午节的时候,母亲早早起来,开始为一家人准备节日的美食,发面,烫面,用红糖面粉拌成馅子,早早吃过早饭,她就一个人开始忙起来,支起油锅,开始为我们炸油条,油糕,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忙,最多让一个孩子烧火就可,几个小时过后,母亲为一家人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一大盆油条,油糕,当孩子们享受食物的美味时,母亲露出开心的笑容,而她自己仅仅吃一点,问她为什么不再吃了,她说自己忙碌了大半天,油炸的油烟味她闻的不舒服。母亲每天早早起来,烧开水,打扫院落,为一家人准备一天的饭菜,她做得每顿饭菜都是那么可口,我小时候常常帮母亲烧火,母亲常为我烤些馍块,红薯。每年农历2月初2,龙抬头那天,母亲会为我们炒些黄豆黑豆棋子豆【用面粉做成两厘米大的小块,晒干,里面有盐和调料】,烤健健馍【一种像鸟,像鱼,像虫子的关中花馍】,每家的孩子比谁家的馍烤的黄而酥,而这一天母亲还会为我煮两个鸡蛋,虽然家里养了十几只鸡,但鸡蛋多是卖钱用的,一家的柴米油盐钱,全是从卖鸡蛋支出,除了来贵客,平时很少能吃到1鸡蛋,那时的鸡蛋真好吃,母亲常说,鸡的蛋,粮食换,那些鸡,是母亲的小银行,我常常到田野里捉蚂蚱,用狗尾巴草穿起来,常常能捉五六十只,回来就全部喂这些鸡,我现在才知道那时鸡蛋好吃的原因。知了在巷子外的大树上开始唱歌的时候,母亲开始为织土布准备了,把纺的棉线用十几穗子插在锭子上,然后用一个大轴卷起来,为了让织的土布漂亮好看,她在此前,还要把棉线染色,天蓝色,红色,最后,再把有颜色的棉线按一定的规律排开,卷在轴上,冬季农闲时,母亲的织布机就有节奏的响起,一丈丈结实好看的棉布就织了出来,每天夜晚,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我们淘气扯烂的衣服,或者摇起纺车,纺棉花,记忆中的母亲,是那么和蔼,勤劳,善良,心灵手巧。她爱孩子,从不骂我们,打我们。尤其爱她的最小的儿子,我。记得我每次闯了祸,父亲打我的时候,母亲总是护着我,有次,不知什么原因,父亲用笤帚把打我,在灶房烧火的地方,我被打的没处躲,母亲上前制止父亲,父亲正在气头上,打我的笤帚把竟落在母亲的身上。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天天忙的不可开胶,用简单的食材,为我们准备过年的美味,腊月20后,母亲便开始和孩子们一起把每间屋子,彻底打扫一遍,上房,厦房,门房。旮里旮旯,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把土炕的上面铺的也要接起,彻底打扫,然后就开始蒸年馍,用自己磨得面粉,头道和2道面粉,头一晚上就起面【发面】,用自己做得酵子,把土炕烧热,一大早,天麻麻亮,母亲就早早起床,开始蒸年馍,通常要蒸一整天,4,5大锅,每大锅有300多个年馍,蒸出来的年馍,又白又香,散发着麦子的香味和酵子的清香,加油泼辣子,一个7,8岁小孩就能吃3,4个。蒸出来的年馍,要在薄子【用高粱秆或狼尾巴蒿织成的帘子,用来晒农作物】晾凉,最后装在瓮里,在没冰箱的年代,瓮,瓦罐,等器皿是贮藏食物的好东西,年馍作为主食,是关中农村过年的必备品。腊月27,28,母亲开始煮肉,蒸碗子,除夕那天,母亲把过年的所有物品·都进所能的准备好,母亲常说,孩子过年,大人过难。
秋天玉米成熟后,父亲把玉米叶子一个个辫起来,然后架在门房的大梁上,一则为了节约空间,二则便于玉米自然通风干燥,防止玉米霉变。我还记得天气炎热的时候,皎阳似火,母亲在做饭,炊烟弥散在门房的每个角落,父亲悠闲地坐着门房的走廊里,大门半开,习习的穿堂风,从门外吹进来,父亲看着医书,面前一张方桌,泼上浓茶,收音机里传来了悠远,动听的秦腔,巷子中,只有知了的叫声彼此起伏,树荫在慢慢的移动,这时候,我感到是最幸福的时候,而我喜欢捉苍蝇喂蚂蚁。 过了门房,来到厦房前,如今,温馨,处处流淌着幸福的两间屋子,已挂满了蛛丝,布满了尘土,曾经整洁,干净的院子,杂草丛生,院子原本是青砖铺设的地面,如今已是面目全非,第一个屋子,是父母和我的卧室,兼具会客厅功能。原来的时候,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顶竖柜,用天然生漆漆成的红木家具,7,8个成人才可移动,父亲常常把柜子擦得明光可鉴,侧面是张很古老的桌子,两边·配着两把古交椅,最里面是古董架,放在一个很古旧的竹子做成的架子上。推开房门,熟悉的气味,熟悉的土炕,依然散发着记忆中的味道,空气中依然流淌着父亲淡淡的旱烟的烟草味,我屏住了呼吸,眼前又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冬日里,母亲把土炕烧的热热的,上面铺上被褥,即使室外天气再冷,走进屋内,脱掉鞋子,坐在土炕上,把脚和腿部伸进暖暖,甚至发烫的褥子里面,会感到人如同晒太阳的猫一样懒得挪动一步,倘若遇到艳阳天,和谐,幸福,白亮亮的冬日阳光照在土炕上,那最好。母亲常常坐在温暖的土炕上,开始做针线活。我小时候喜欢在土炕上翻滚打斗,母亲常劝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土炕的泥基踩烂。老屋的窗户是古老的木制窗户,像门一样可以开关,外边是几根竖木,很像今天的防盗网,最外边是格子窗,可以装卸,在上边贴上白纸麻纸,或者纱,一则美观,二则实用,姐姐用红红的纸张,剪成美丽的窗花,有各种小动物,各种花草,贴在窗户上。让人呆在屋外,就能感受到家的温馨和幸福。每天傍晚,母亲烧好一大锅煎汤,父亲一边喝着酽茶,一边和朋友谈古论今,悠闲自在,一副把酒话桑麻,还来就菊花的写照。 最后边是上房,高大明朗的传统古建筑,真正的砖木机构,房屋的建造完全按照先‘’立木,后墙体‘的建造法建造,每面墙里都有几个大木柱子’起承重和骨架作用,而这些柱子又通过榫卯结构和几个大梁连在一起,房屋的屋顶有许多脊兽,青色的瓦片像鱼鳞一般覆盖在上边,屋檐处的瓦片成七字型,俗称滴水瓦,上面雕刻着图案,大约是猫面或者狗面的图案。房屋用青砖和白灰砌成,青砖比现在的二四红砖大许多,厚许多。砌墙的白灰用水过滤,然后沉淀,砌的砖缝要像白线一样细细的才是合格。地面是用方砖铺成,由于年代久了,许多方砖以碎成小块,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上房除了破旧外,依然可以看出传统建筑科学和大气之美,人们常说,人是房屋的精灵,没人住的房屋,要不了几年就破烂不堪。在看过党家村的明清古建筑群后,觉得老屋的上房比党家村的祠堂还建的好。其实,在大荔朝邑,曾经·有许多这样的民宅和古建筑,在缺乏保护和岁月的洗礼中慢慢消失。今天,仿古建筑,仿古镇大行其道,而真正的古建筑,古镇却无人问津。从高高在上,张扬的各种办公建筑和以假充真,浮躁的仿古建筑上我们能读出时代的音符。
(供稿:祁宏涛)
![图片[1]-陕西省监狱管理局:老屋-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acbc3a54d7081135.webp)
![图片[2]-陕西省监狱管理局:老屋-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607ce44185b2d407.webp)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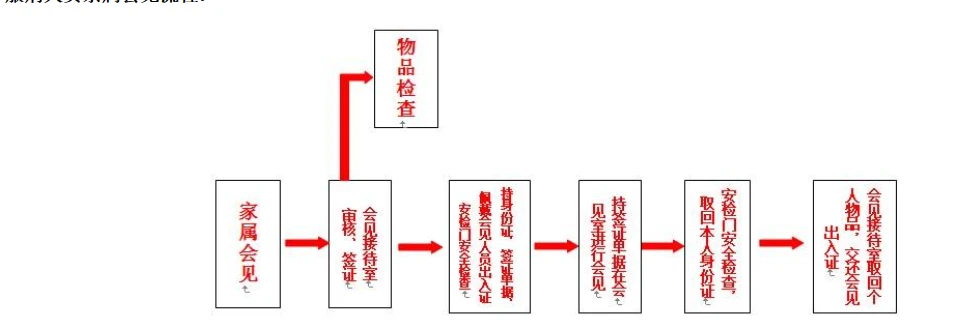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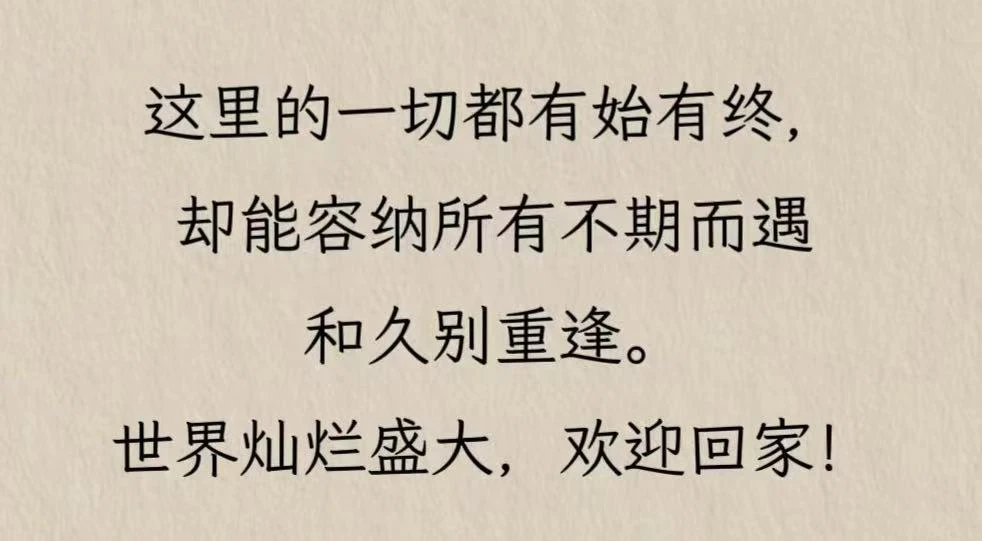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