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盛开时节,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包幼蚕,白白的,蠕蠕的,像一颗颗饱满的米粒。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不好意思的说:“这是邻居送的,到时候还要还给人家,保证不影响带孩子!这种生物只是在科普读物上见过,我也很好奇。”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母亲在阳台的地板上铺了一张牛皮纸,撒上剪碎的嫩桑叶,把幼蚕摆上去。我数了数,有90多只呢。四月初的时候,蚕宝宝已有两厘米左右了,肉嘟嘟的,到处乱爬。为了保证蚕宝宝充足的活动空间,母亲把蚕和桑叶小心翼翼地移到“新房子”里,那是一个剪成两半的废纸箱。夜深人静的时候,常能听见里面“嚓嚓嚓”的咀嚼声。
母亲对养蚕很是上心。一天晚上,母亲从外面提着一袋鲜桑叶回来,全身湿湿的。唉,今天差点把这把老骨头扔在汉中了!母亲长吁一口气说。原来是下旬的时候,市里下了几天雨,在农村生活已久的母亲在小区闷了好几天。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母亲在下午的时候打伞到外面转转看看,顺便到龙岗大桥附近一带的沟地里采集桑叶,却因路湿差点滑进一口当地村民用来储存灌溉用水的井里。那天晚上,母亲洗净双手,戴上眼镜,拿湿布把一片片桑叶擦拭干净,摆在阳台风干后,又整整齐齐装入保鲜袋放进冰箱冷藏起来。母亲说,蚕生命虽短,却是善虫,实在是舍不得也不忍心扔掉,一定要给吃干净的桑叶,沾过生水的桑叶最致命。我没有接母亲的话,因为我知道这是不习惯城市生活的母亲在闲暇时间充实生活、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
在母亲的精心照看下,蚕宝宝健康的成长着,一天一个变化。那些日子,连两岁的女儿都经常嘟哝“喂虫虫、喂虫虫”。劳动节的时候,蚕已长成小拇指大小了,全身黄亮黄亮的,顺着纸箱向上爬。母亲从外面收集了一把竹枝,用绳子从尾端扎紧,轻轻地把一条条蚕捏上去,蚕一会爬上,一会爬下,在竹枝上来回游走,就像年迈的母亲在汉台、洋县之间来回奔波一样。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这几年为了照看我的孩子,撇下了农活来到了汉台。她常说人老了就闷得慌,就在孩子睡着后、安静时承包了大半的家务活。她还常给我说,你忙你的吧,监狱人民警察担子重,责任大着哩!
不到三天时间,90多只蚕宝宝全部结了茧,圆鼓鼓,软绵绵,有黄的,有白的,远看好似一束彩色的棉花糖。记得小时候,家乡的老人们常在稻香季节把茧放进大锅里煮,火候一到,顺势一捞,蚕丝就出现了。没错,这正是两千多年前流行于欧亚大陆上中华瑰宝的原材料吗?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欧洲贵族为了穿上中国的丝绸而不惜豪掷重金,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一个空闲的下午,母亲把一颗颗“棉花糖”从竹枝上摘了下来,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依依不舍地送给了邻居。从我的牙牙学语到懵懂懂事,从十年寒窗到步入工作、结婚生子,母亲拼搏了一辈子,坚忍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那天,我看见了母亲头上的一根根白发,好似一把把蚕丝。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有人喜蚕的顽强生命力,有人爱蚕的默默奉献精神,有人觊觎蚕的滋生财富,我却钦佩蚕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蚕不求索取,只为奉献,以永不懈怠的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姿态度过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留下了丝,留下了财富,留下最多的却是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图片[1]-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母亲与蚕-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16c38347422aed76.webp)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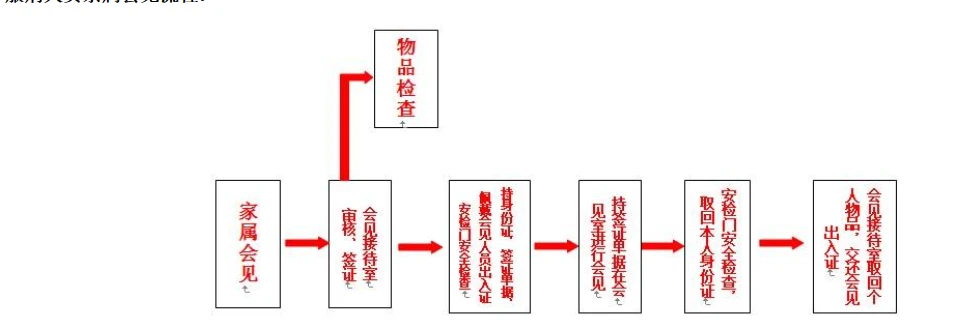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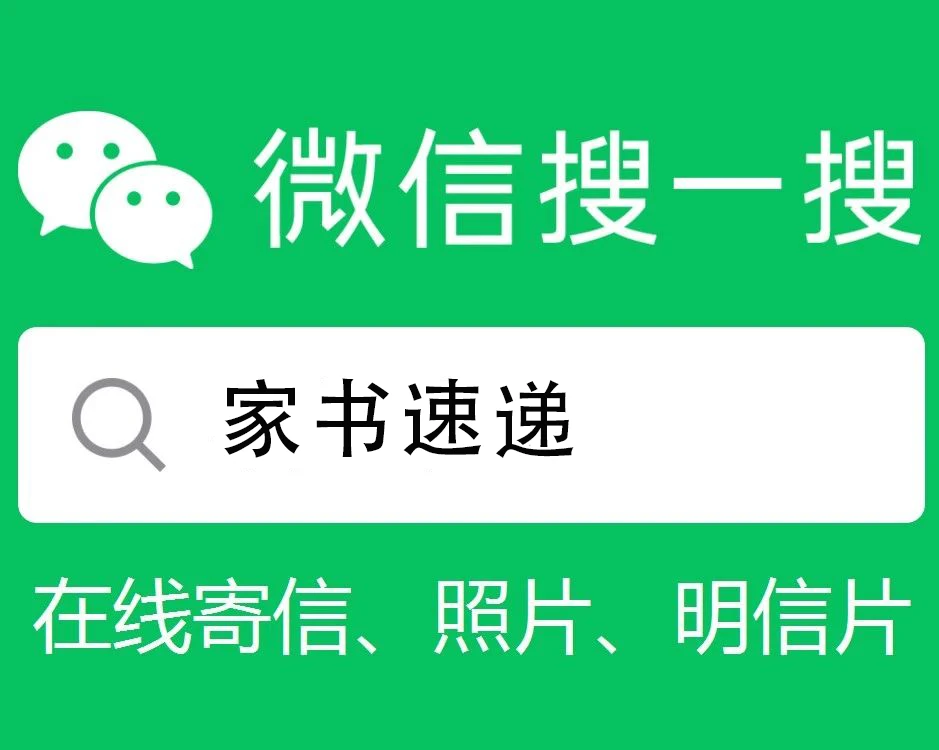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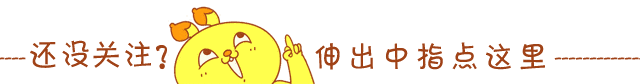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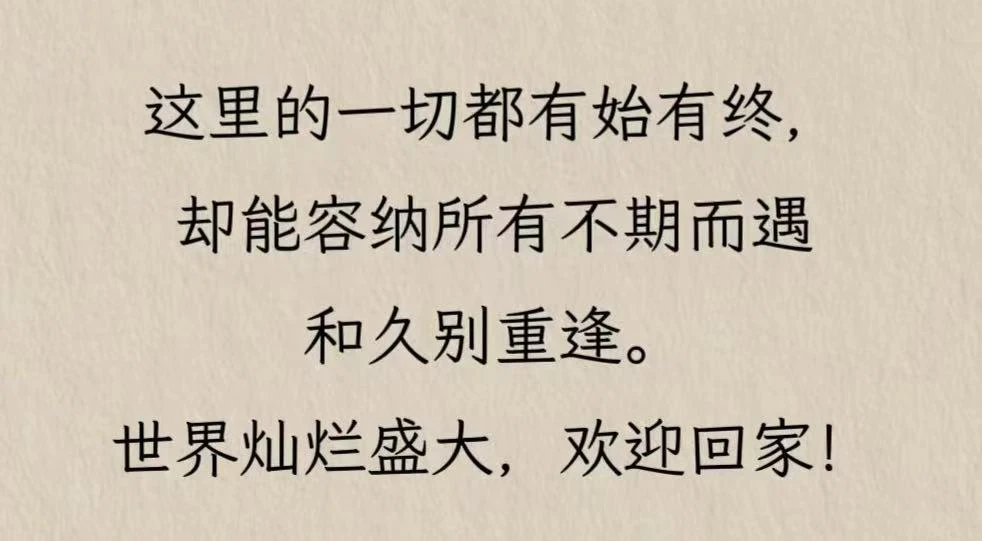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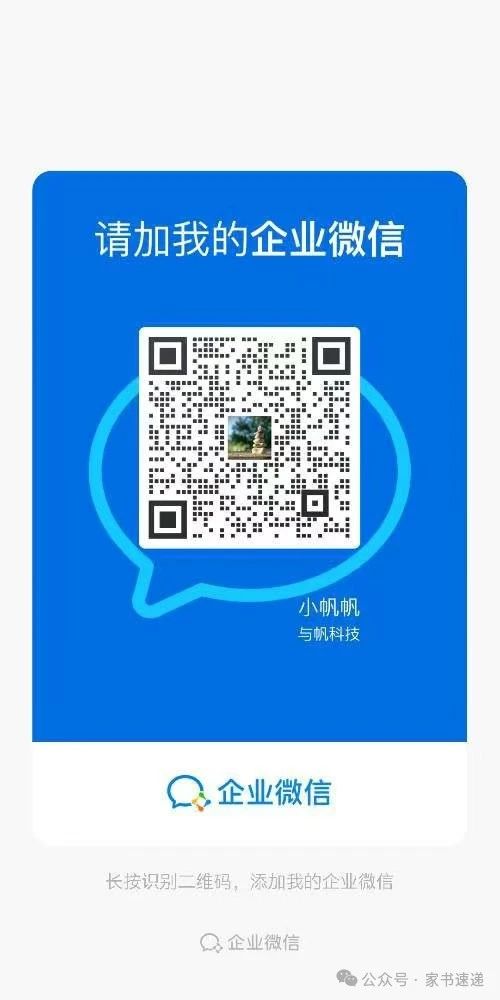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