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的核心环节在于责任的划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直接关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承担行政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可诉性问题,长期以来纷争不断。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的演变脉络,剖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到被《道交法》定位为“证据”而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的完整历程,进而对其当下的法律属性进行再界定,并对相关救济途径进行评析,以期为理解这一制度的“前世今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法律图谱。
一、早期规定与司法实践的探索阶段(1992年《办法》施行至2004年《道交法》出台前)
在《道交法》颁布之前,我国交通事故处理的核心依据是国务院于1992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与此配套,公安部于1992年8月10日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号)第二条明确了处理主体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在第三十二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出后,应当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从行政法学理论视角审视,这一时期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第一,作出主体是依法享有道路交通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第二,行为内容是针对特定交通事故中的特定当事人,就其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第三,行为后果将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仅关系到民事赔偿的分担,还可能成为追究行政责任(如罚款、吊销驾照)乃至刑事责任(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根据。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进行司法审查,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
然而,司法实践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9号),其中第四条明确:“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事实上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可诉性关上了大门,但同时也引发了持续的争论,认为其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限制当事人的诉权,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存在冲突。
转机出现在世纪之交。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一条第一款对可诉行政行为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规定。在此背景下,一些法院开始进行突破性尝试。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在2001年第五期和2002年第五期分别刊登的“李治芳不服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案”与“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在这两个案件中,人民法院不仅受理了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的诉讼,而且经审理作出了撤销重作的判决。尤其在“罗伦富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对责任认定行为的性质作出了深刻阐述:“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该论述清晰地揭示了责任认定行为对当事人产生的法律效果,有力地论证了其接受司法审查的必要性。这两个公报案例的发布,犹如投石入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涟漪效应,各地法院纷纷参照受理此类案件,形成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的一个短暂“窗口期”。
二、《道交法》的颁布与制度根本性变革(2004年至今)
2004年5月1日,《道交法》的施行,成为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法律属性的分水岭。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与《办法》相比,此条文有两处至关重要的修改:其一,在法律文书名称上,以“交通事故认定书”取代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删除了“责任”二字。尽管认定书的核心内容依然是对当事人责任的划分,但这一文字变化传递了立法者企图弱化其独立行政行为色彩的信号。其二,也是最具颠覆性的,是明确增加了“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这一法律定性。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责任认定的角色,使其从一种可被独立挑战的行政决定,转变为在后续诉讼程序中使用的证据材料。立法者此举的考量,或在于兼顾处理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避免因对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责任认定行为开启行政诉讼之门而导致案件审理周期过长、程序空转。
为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法律适用,2005年1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的请示,作出了《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法工办复字〔2005〕1号)。该答复明确指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一具有立法解释性质的权威答复,彻底终结了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可诉性的争论。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制度。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二十七条(该司法解释于2020年修改后,该条内容调整至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该规定明确了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职责与采信规则,即其并非免证事实,其证明力需经法庭质证和审查,当事人有权通过提供充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甚至推翻。
三、法律性质再辨析与现行救济途径评述
然而,“不可诉”不等于“无救济”。现行法律框架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的当事人设置了以下救济渠道:
第一,行政复核程序。根据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46号)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法定时限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交管部门经审查,若认为原认定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责任划分不公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的复核结论。”复核程序作为一种内部行政监督机制,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的首要和快捷途径。
第二,证据审查。这是当前最主要的救济途径。在因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质疑,并提交相反证据(如现场照片、证人证言、专家意见、行车记录仪视频等)来挑战其证明力。人民法院负有依法审查证据的职责,必须对认定书的结论进行实质性判断,而非无条件采纳。若当事人提供的相反证据足以构成合理怀疑或推翻认定书结论,法院则可不采信该认定书,并根据庭审质证情况自行认定案件事实和划分责任,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司法审查”。
四、结语
回顾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30余年的法律变迁,其轨迹清晰地描绘出一条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到“法定不可诉的行政确认行为”,同时作为“需经司法审查的证据”的演变路径。这一演变并非简单的倒退或前进,而是立法与司法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权衡行政效率与司法公正、专业判断与权利保障、程序便捷与实体正义之间复杂关系的动态平衡之结果。它将专业性问题交由行政机关初步判断,同时通过复核的行政监督与诉讼程序中的证据审查机制,保留了司法最终裁决的底线,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模式。
理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前世今生”,不仅有助于法律从业者准确把握现行规则,更能够深刻体认我国法治建设在具体领域不断走向精细化、理性化的演进逻辑。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 :刘万金 崔静星
该文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前世今生”》来源于家书速递,网址:https://www.jiashusud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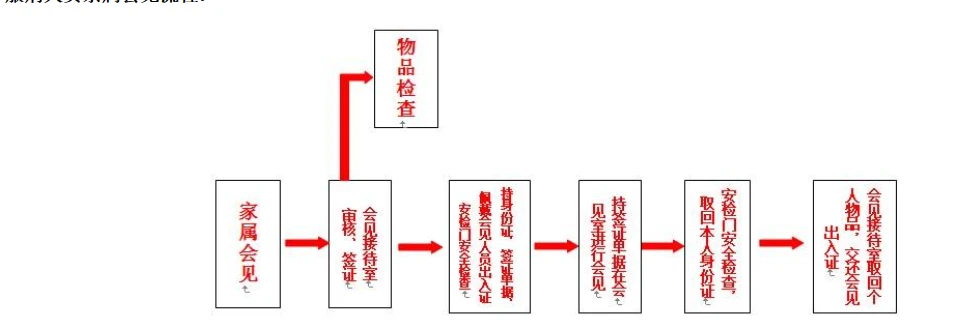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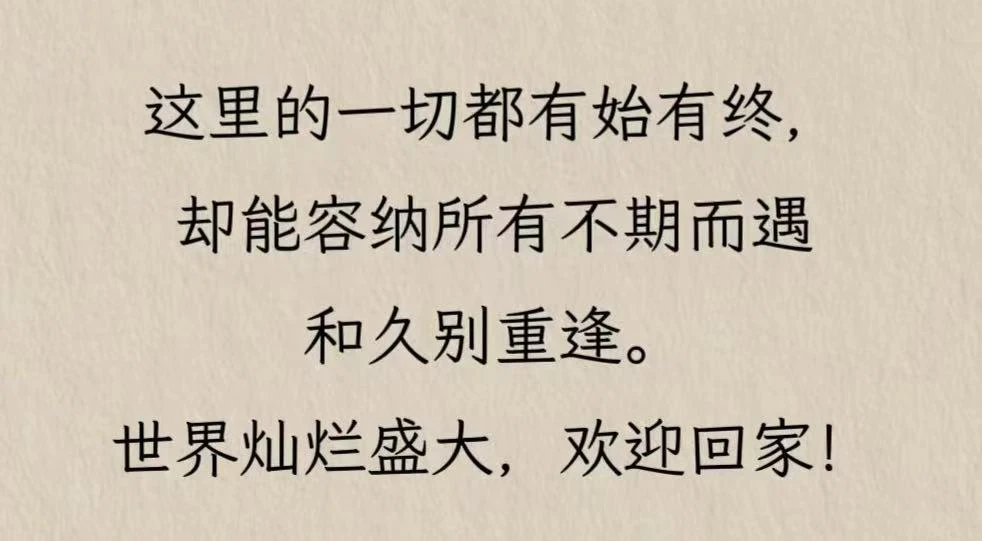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