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是久盼的春节,原以为是一场久别重逢,是兄弟姐妹的相聚,是承欢膝下在老父亲跟前,是他虽卧床不起,却眼巴巴地盼了又盼,我们可以叙亲情,可以尽孝道,可以让他享天伦之乐,可以让他感受从外面带来的有新意的儿女情。
我们早早盘算着,女儿甚至还准备了不甚解的问题,准备请教大舅二舅,姐夫也早早准备好招待的肉鱼果菜,哥嫂从四川提前邮好了血橙、泰蕉、芒果,我们热热乎乎地聊着,只为那一刻的相聚,也想让他们看看家乡的变化,沿着洛河长堤,村庄已今非昔比,绿化带已具规模,河边风景初现,已成了锻炼的好去处。
年味愈浓,天气渐暖,但是今年疫情又有复燃苗头,春运人员流动大,国家提倡原地过年。于是,先是哥退了回来的票,决定留四川过年,等父亲生日再回来。
团聚的愿望如焰火渐暗,让我们的心多了几丝沮丧,但是疫情形势严峻,我们接受了。临近过年,回老家照顾老父亲,依惯例烧火炸闲食,并且逗他说,“这搁以前,可是你的差事啊,现在你咋不干了?真会偷懒。”他咧嘴笑了,也透着难以言表的心酸。
弟弟还是单身,平时忙,决定尽量从广州回来团圆,因为父亲身体情况不容乐观,而在老家,姐姐仍日夜照顾着老父亲。
少聚餐,做好防护,开始了细水长流的家居生活。
我重新看《家园与乡愁》,是副刊文丛,借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当读到《大地湾》时,被其中的一段文字打动“我童年的时候,还处在古老农业社会的尾巴上,那是一种慢生活,朴素、清贫,但并不贫乏,清贫里透出几分谨慎和对人间情义的看重;节制、缓慢,但并不凝滞,缓慢里自有一种令人静下来细细品味的田园意境和乡土古风。”
和我现在的状况何其相似,慢节奏让我走近淡泊。而“那种慢,是扎根于农历里、轮回于四时八节里、传唱于农谚歌谣里、氤氲于乡风民俗里、鲜活于鸡鸣鸟叫里、往返于麦浪稻香里、掩映于杨絮柳烟里的慢。”
我在乡间长大,又在城市里寄居多年,平时忙碌为工作,为生活,而闲聊时间沉浸在自己的田园牧歌里,总是在文字里扑捉那份久违了的安然恬静,找到心灵的归属和宁静。
这两年不期而遇的疫情,让我得以审视自己的生活,究竟在无尽的物欲和得到中丢失了什么,那些荡漾在心头的绿色和飘在家乡上空的云,清风拂过的小河,曾轻承载过多少未知、诗和远方。
我努力奋斗,离开家乡,走向自以为的繁华,违背了自己的初心,寻寻觅觅是为了什么,锦衣玉食终是浅薄,人际关系的疲惫和不善于此,是我格外留恋、回味那乡间的野花阡陌,我终是把灵魂丢在那儿、留下了。
兜兜转转中,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过客,率真自然,保持本色是我的原色,所幸我没有迷失,走得太远。而读到“连小河的流水都是慢悠悠的,生怕带走了一河倒影和两岸风情。缓慢里,日子就有了天长地久没有结尾也不会有结尾的感觉,古朴厚道的人们,有的是时间,去静心播种人间的情义,去感受山川万物的意味。”
这一点我是欣慰的。厚道待人,邻里和睦,和谐相处是依然保持的。而我大部分时间,工作之外,是流连在公园的花木丛中,是在和同伴的热聊中,有时在春天去看一场花事:樱花海棠,桃李芬芳;夏天去竹林寻幽,观荷避凉;秋天去蔷薇深处,银杏地黄;冬天去踏雪寻梅,徜徉书房。在城市的每一处,找到自然的着痕,月色风声,微波不惊,都是赏心悦目所在啊。
正所谓心安即故乡,何处不风景。在居家的日子,女儿写作业,补网课,也渐充实;打斗地主,下五子棋,进步神速;码字读书,丰富了内心,呼唤着沉寂的往事;难得的家庭融融。
许久没有这样了。柴米油盐的日常充斥着我的生活。俗了又俗的曾经不屑为之的事情是我必做的功课。能在这来去匆匆的时光中过一段慢时光,是我不得已却无意称意的选择,远离焦灼,沉淀自我,而且勾勒出了一幅岁月静好安稳,我自不惊不扰的节拍图。
这一切感谢我所在的城市,和无数忙于防疫防控,进行疫情演练,防患于未然。
今年定是好的开端,虽然多少人有未了的心愿,未能成行的团圆,但是如果能共渡难关,共同抗疫成功,经济复苏,结局也是好的。这是无数平凡勇敢者的壮举,也是无数坚守、囿于斗室的人们的贡献,只愿人长久长安,一起走向繁花与共的春天!
![图片[1]-陕西省监狱管理局:走向宁静,走向春天-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607ce44185b2d407.webp)
![图片[2]-陕西省监狱管理局:走向宁静,走向春天-家书速递|在线寄信|网上寄信|寄信软件|监狱寄信|看守所寄信](https://www.jiasusd.com/uploads/202411/14/1d6e8e973b4ab9a2.webp)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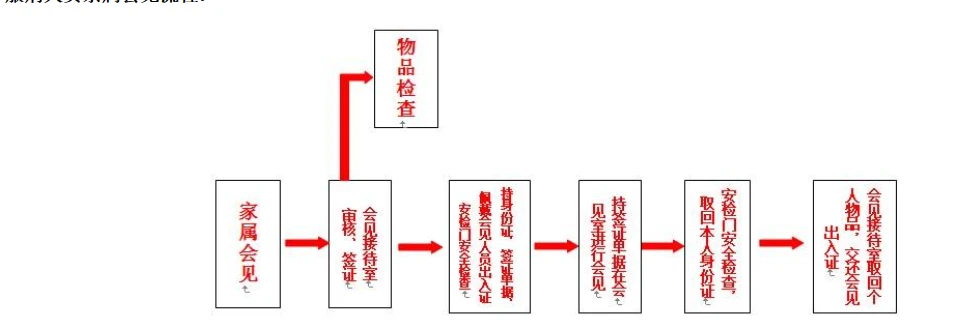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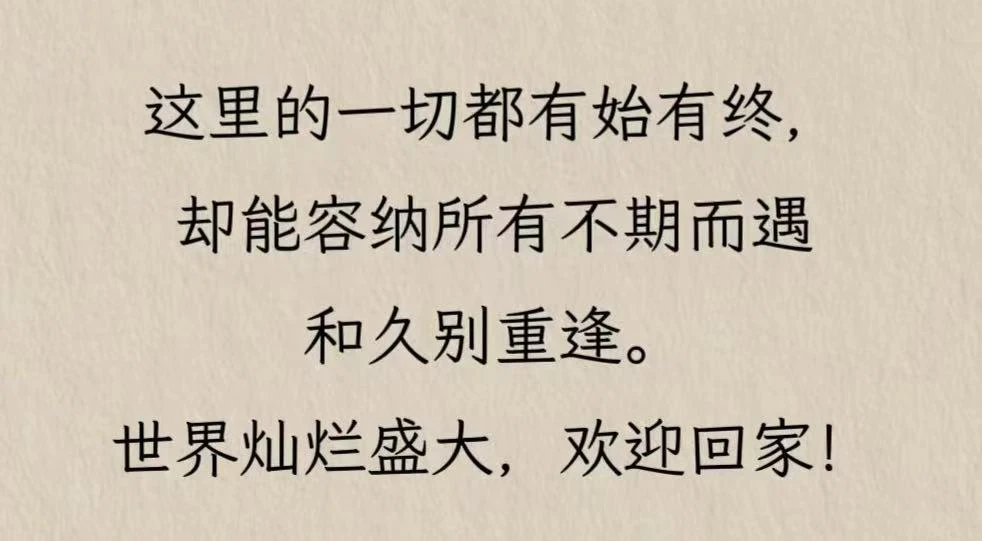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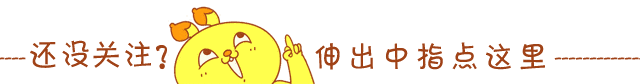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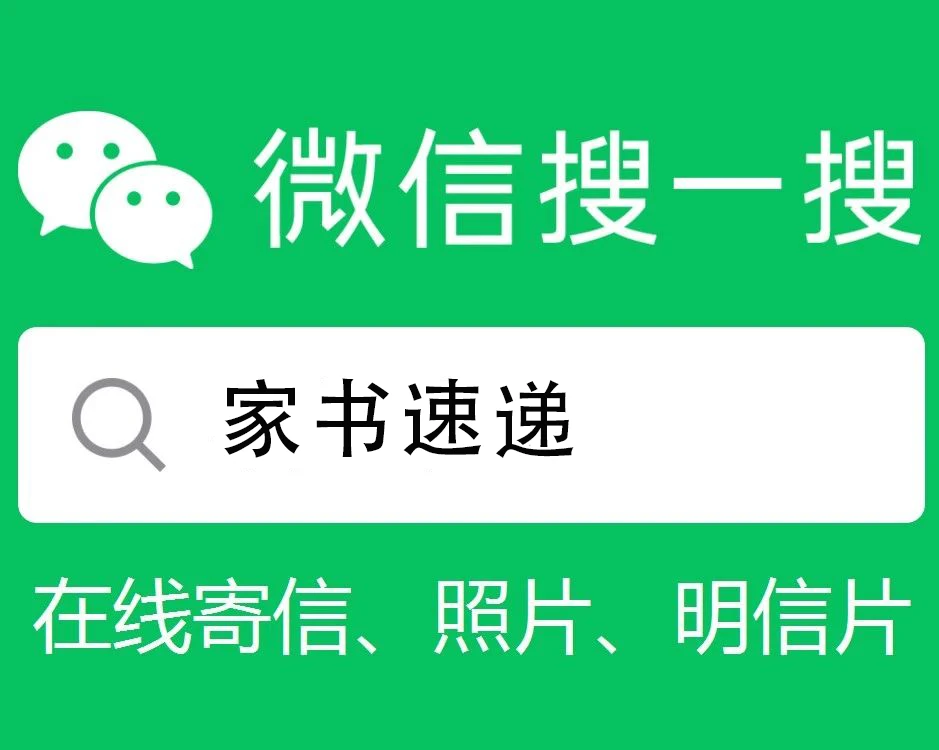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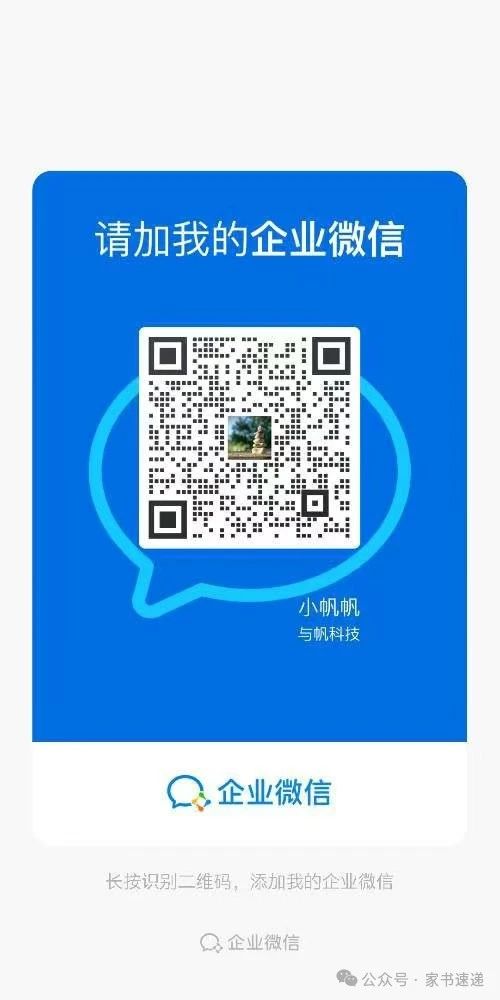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